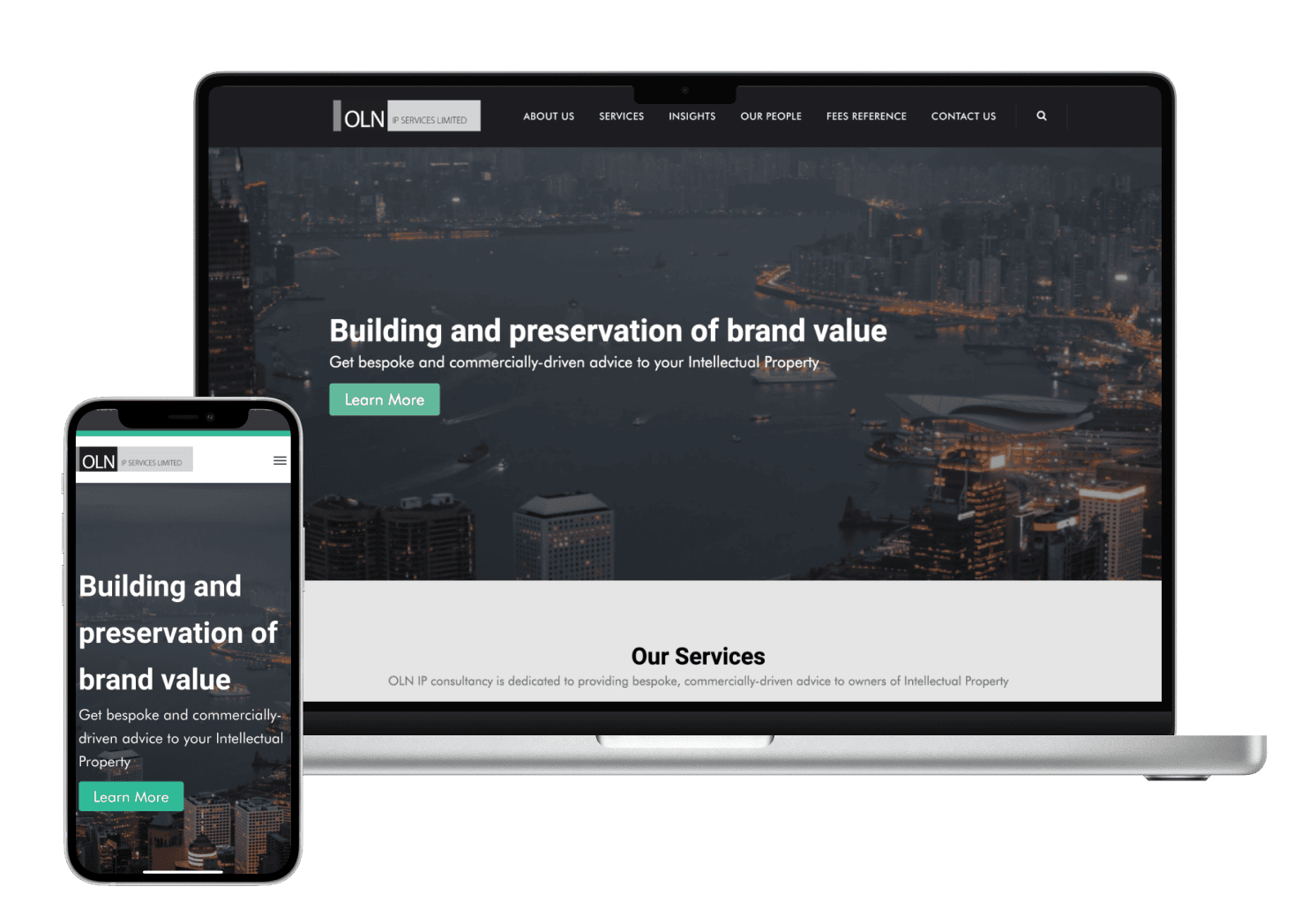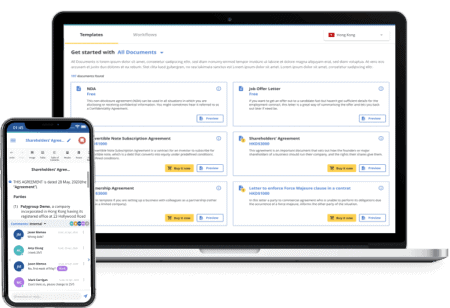Oldham, Li & Nie (OLN) is pleased to announce its participation in the 2024 Hong Kong Arbitration Week, organised by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HKIAC), taking place on 21-25 October 2024.
The firm will host a panel session titled “Arbitration and Justice: the Compromise on Insolvency, Illegality and Conflicting Arbitration Clauses?” on 22 October 2024 from 5:00 to 6:30 pm.
This debate session will critically examine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arbitration and substantive/procedural justice in light of the latest case authorities, including:
- Sian Participation Corp (In Liquidation) v Halimeda International Ltd [2024] UKPC 16, Re Simplicity & Vogue Retailing (HK) Co., Limited [2024] HKCA 299, and Arjowiggins HKK 2 Limited v Shandong Chenming Paper Holdings Limited [2024] HKCA 352: The availability of bankruptcy / winding-up tools for arbitration-governed debts
- AAA v DDD [2024] HKCFI 513: The complication of incompatible arbitration clauses in multi-contract transactions
- G v N [2023] HKCFI 3366: The interplay between arbitration and illegality
The session promises to deliver a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these critical issues from various expert perspectives.
The distinguished panel will feature:
- Prof. Anselmo Reyes, International Judge at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SICC)
- William Wong SC, Barrister at Des Voeux Chambers
- Frances Lok SC, Barrister at Des Voeux Chambers
- Sarah Thomas, Associate General Counsel of McKinsey & Company
They will be joined by OLN’s lawyers, Partners Dantes Leung and Jonathan Lam, with Associate Davis Hui serving as the moderator. Each panelist will offer unique insights, contributing to a robust and enlightening debate.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2024 Hong Kong Arbitration Week, please visit https://hkaweek.hkiac.org/event/f3e694d2-39ac-451c-aa66-cb9d9af52bc2/summary.
To register, please visit https://hkaweek.hkiac.org/event/f3e694d2-39ac-451c-aa66-cb9d9af52bc2/regProcessStep1.
For information about our arbitration services, please contact our Partner Jonathan Lam.
 香港中环雪厂街二号圣佐治大厦五楼503室
香港中环雪厂街二号圣佐治大厦五楼503室 +852 2868 0696
+852 2868 06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