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provide the best experiences, we use technologies like cookies to store and/or access device information. Consenting to these technologies will allow us to process data such as browsing behavior or unique IDs on this site. Not consenting or withdrawing consent, may adversely affect certain features and functions.
The technical storage or access is strictly necessary for the legitimate purpose of enabling the use of a specific service explicitly requested by the subscriber or user, or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carrying out the transmission of a communication over an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
The technical storage or access is necessary for the legitimate purpose of storing preferences that are not requested by the subscriber or user.
The technical storage or access that is used exclusively for statistical purposes.
The technical storage or access that is used exclusively for anonymous statistical purposes. Without a subpoena, voluntary compliance on the part of your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or additional records from a third party, information stored or retrieved for this purpose alone cannot usually be used to identify you.
The technical storage or access is required to create user profiles to send advertising, or to track the user on a website or across several websites for similar marketing purposes.
 香港中环雪厂街二号圣佐治大厦五楼503室
香港中环雪厂街二号圣佐治大厦五楼503室 +852 2868 0696
+852 2868 06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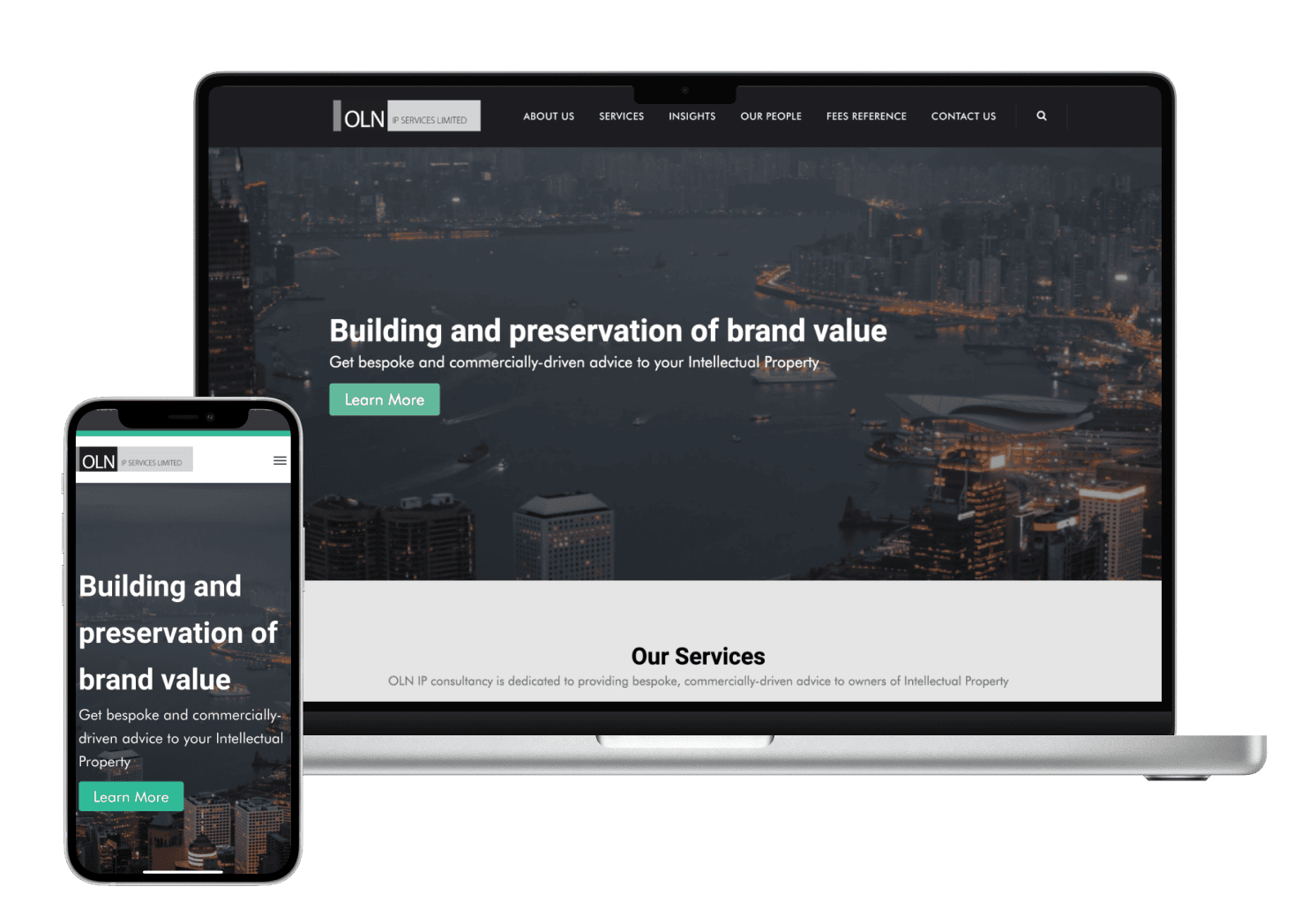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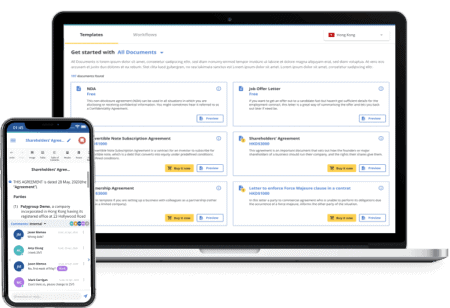



 . However, this was initially declined for registration in Class 25 for “clothing” in China because of the word “FRANCE” within the trade mark. Ms Van Damme succeeded in the review by convincing the review adjudicator that the word “France” is generally perceived by consumers, in the context of her brand, as the name of a living person instead of referring to the country of France.
. However, this was initially declined for registration in Class 25 for “clothing” in China because of the word “FRANCE” within the trade mark. Ms Van Damme succeeded in the review by convincing the review adjudicator that the word “France” is generally perceived by consumers, in the context of her brand, as the name of a living person instead of referring to the country of France.  was initially declined for registration in Class 9 for “loudspeakers” in China because of the word “URAL” in the mark being associated with the
was initially declined for registration in Class 9 for “loudspeakers” in China because of the word “URAL” in the mark being associated with the  was initially declined registration in Class 4 for ‘fuels’ as the words ‘CAR’ and “DRIVER” seem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products of “fuels” for automobiles but if we look at these words more carefully, they are not directly connected to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the goods. The Applicant succeeded in the review by convincing the review adjudicator that the mark as a whole is not directly descriptive of the goods sought to be registered and it is capable of functioning as a trade mark to indicate the source of origin of the goods.
was initially declined registration in Class 4 for ‘fuels’ as the words ‘CAR’ and “DRIVER” seem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products of “fuels” for automobiles but if we look at these words more carefully, they are not directly connected to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the goods. The Applicant succeeded in the review by convincing the review adjudicator that the mark as a whole is not directly descriptive of the goods sought to be registered and it is capable of functioning as a trade mark to indicate the source of origin of the goo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