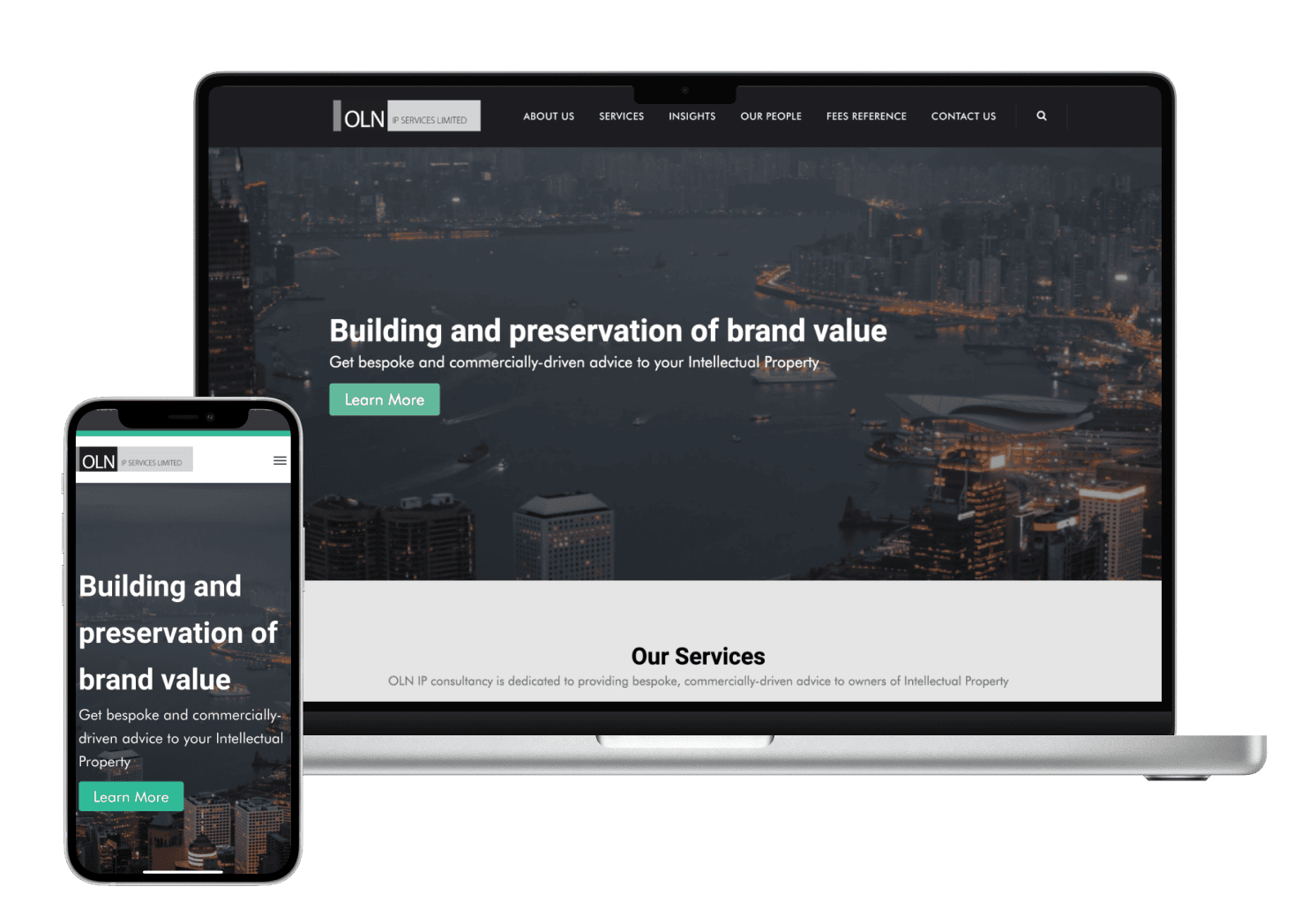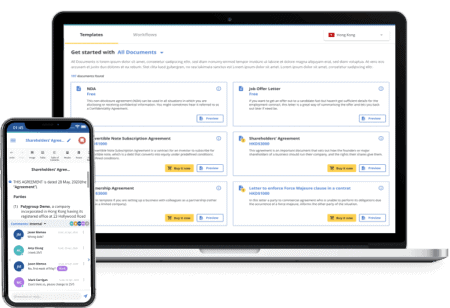理解仲裁庭管轄權和申索的可受理性之間區別: 當白天變成黑夜
(這篇文章發表在 2023年四月香港律師會會刊 )
引言
多重仲裁協議,即普遍要求合約雙方在進行仲裁前進行善意談判或調解,並不罕見。儘管當事人可能合理地期望仲裁只應於仲裁前要求獲遵守後進行,現實或會讓人意外。
在 C v D [2021] 3 HKLRD 1 (HKCFI);[2022] 3 HKLRD 116 (HKCA) 中,香港法院考慮了若當事人不遵守仲裁前要求而進行仲裁,是否構成對仲裁庭理解仲裁庭管轄權的挑戰。香港原訟法庭和上訴法庭基於仲裁庭的管轄權與申索的可受理性兩項概念之間的區別,裁定除非當事人另有明確說明,否則不遵守仲裁前要求屬「申索可受理性的問題,而非仲裁庭管轄權的問題」。由於此項挑戰被裁定在本質上不涉及仲裁庭的管轄權,法庭不能審查裁決的正確性。因此,正如 C v D 案一樣,不論仲前要求是否獲遵守,仲裁庭仍有管轄權而仲裁實際上可以進行。這顯然違背當事人的合理期望。本文將批判地審視仲裁庭管轄權與申索可受理性之間的區別,以及 C v D 案的理據。就本文而言,我們假定「除非 X,否則不得提起仲裁」和「在 X 的情況下,雙方可進行仲裁」並 無 區 別(Republic of Sierra Leone v SL Mining Ltd [2021] EWHC 286 (Comm))。本文將論證最終的問題是挑戰是否涉及仲裁庭的管轄權。我等謹提出挑戰如關乎仲裁前要求未獲當事人遵守,則應被定性為涉及仲裁庭的管轄權。
C v D
在 C v D 案中,C 對 D 提起訴訟以撤銷 D 在未遵守仲裁條款內的仲裁前要求的情況下獲得的部分裁決。該仲裁條款要求雙方須先嘗試進行為期 60 工作天的真誠談判,然後方可將任何未解決的爭議提交在香港進行的仲裁。
香港原訟法庭裁定而香港上訴法庭隨後確認,C 的挑戰涉及的是申索的可受理性而不是仲裁庭的管轄權,因此法庭不會審查有關裁決的正確性。法庭的理由如下:
- 仲裁庭的管轄權與申索的可受理性之間存在區別。
- 正如新加坡上訴法庭在 BBA v BAZ [2020] SGCA 53(關於時效的挑戰)和 BTN v BTP [2020] SGCA105(關於已判事項的挑戰)中解釋,區別仲裁庭管轄權與申索可
受理性的測試實質上是「仲裁庭相對申索」的測試,即該挑戰是否針對仲裁庭(由於仲裁協議出現缺失或遺漏,該申索不應進行仲裁),還是針對申索本身(由於該申索自身存在缺陷,故根本不應提出)。在這兩宗案件中,新加坡上訴法庭裁定,基於時效和已判事項的挑戰僅針對申索本身,性質上不涉及管轄權。 - 管轄權和申索可受理性之間的區別可能模糊不清,有時難以知道兩者甚麼時候開始及終結,就像白天過渡至黑夜時,總有暮色時分(Robert Merkin and Louis Flannery, Merkin and Flannery on the Arbitration Act 1996 (6th edn, Rotledge 2019), [30.3])。
- 仲裁協議沒有表明當事人意圖把遵守仲裁前要求視為管轄權的問題,而且當事人似乎不太可能意圖在仲裁庭進行全面聆訊和作出決定後,以訴訟方式重啟案件。
仲裁庭管轄權和申索的可受理性:存在區別還是二元對立?
作為一項初步觀察,當考慮挑戰是否涉及仲裁庭管轄權時,香港原訟法庭和上訴法庭均裁定不遵守仲裁前要求涉及「申索的可受理性,而非仲裁庭管轄權」。我等的愚見為這種表述不太合適,因為它隱含了申索的可受理性與仲裁庭管轄權屬二元對立的意思。
儘管申索的可受理性和仲裁庭管轄權之間可能存在區別,但這兩個概念不一定互相排斥,單一事件有可能同時引起對申索的可受理性和仲裁庭管轄權的挑戰。這點可以參考英國上議院在 Fiona Trust and Holding Corporation v Privalov [2007] UKHL 40, [17] 中給出的一個例子:如果同一份文件包含主協議和仲裁協議,而其中一方當事人聲稱他從未同意該文件的任何內容,其簽名亦是偽冒的,則會同時構成對主協議及仲裁協議有效性的質疑。
因此,我等謹認為,在考慮挑戰是否涉及仲裁庭的管轄權時,提及申索可受理性此概念的作用不大。最終問題應是挑戰是否涉及仲裁庭的管轄權(即針對仲裁庭)。
涉及仲裁前要求的挑戰本質上針對仲裁庭的管轄權
分析的出發點是不同案例曾各自歸類仲裁前要求為涉及仲裁庭的管轄權、申索的可受理性或程序的問題(Gary Bor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3rd ed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21), 988-989, 997-999)。公道來說,不同法律體系之間沒有統一的做法。
鑒於意見不一,有人認為在詮釋仲裁前要求時,當事人的意圖應獲考慮,正如香港原訟法庭和上訴法庭聲稱在 C v D 案中所做的一樣。遺憾地,相對於審查挑戰背後的基本事實以確定當事人的真實意圖,香港法庭實際只是宣布有關仲裁的司法政策(例如速度、終局性等),以及相應於當事人意圖的法律推定——即法庭推定當事人有意將仲裁前要求歸於申索的可受理性,故須由仲裁庭專門處理。這種司法政策和法律推定的應用顯然是循環的:當事人挑戰仲裁庭管轄權機制完全在仲裁制度之內,不能說成當事人同意仲裁,即代表當事人為了速度和終局性,意圖將本來應獲適當歸類為涉及仲裁庭管轄權的挑戰視為不牽涉仲裁庭管轄權。香港法庭的做法只是重覆了須適當歸類仲裁前要求的問題。
本文須指出,時效的問題(如 BBA v BAZ)和已判事項的問題(如 BTN v BTP)屬申索的可受理性的經典例子。這些問題質疑「申索」本身(針對一個特定的申索而不是其他潛在的申索),亦沒有以任何形式針對仲裁庭。換句話說,撇開挑戰不談,仲裁庭擁有一般管轄權就任何其他不受時效或已判事項限制的申索作出裁決。
然而,因不遵守仲裁前要求而衍生的挑戰的性質截然不同。仲裁前要求未獲遵守的挑戰不會以時效問題或已判事項問題的方式攻擊「該申索」本身——事實上,仲裁前要求未獲遵守的挑戰並不會攻擊某特定「申索」,而是廣乏針對仲裁協議涵蓋的所有申索,因此除了該些受仲裁前要求約束的申索之外,仲裁庭根本沒有其他事項可作出任何裁決。我等謹認為,這顯示仲裁庭實際上沒有任何一般管轄權。為了進一步闡釋 Merkin and Flannery 第 30.3 段中白天與黑夜的比喻,白天不會因移除了一束光線而變成黑夜,但如果根本沒有光線,那就肯定是黑夜了。無論如何,詮釋仲裁前要求為涉及仲裁庭管轄權的問題也符合當事人的意圖,因為此項詮釋為當事人的意圖提供了雙重保障(即在仲裁庭層面及在法院層面),確保除非當事人遵守仲裁前要求,否則不得進行任何仲裁。
真正的擔憂
法庭真正的擔憂似乎是,當是否進行仲裁是取決於某些仲裁前步驟時,如果一方當事人不採取該些步驟,另一方就可撤回對仲裁的承諾(Alexander Jolles, “Consequences of Multi-tier Arbitration Clauses: Issues of Enforcement” (2006) 72 Arbitra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bitration, Mediation and Dispute Management 329, 335)。這種擔憂是誤解。
即使仲裁前要求未獲遵守,它不會自動容許無錯失的一方退出仲裁協議(Hugh Beale, Chitty on Contracts (1st supp, 34th edn, Sweet & Maxwell 2022), [4-197] – [4-203] )。未遵守仲裁前要求的一方仍可能稍後遵守仲裁前要求以展開仲裁。由於仲裁協議仍然有效、可實行或可履行,《仲裁條例》(第 609 章)第 20 條適用於阻止在仲裁前要求獲遵守之前提起的訴訟。
當然,如果違約一方明確表明不會履行仲裁前要求,則多重仲裁協議可能因預期違約而被廢除。在這種情況下,無錯失一方有權決定是否接受悔約,或仍然選擇仲裁。若無錯失一方接受悔約,當事人的爭議應通過法庭訴訟解決,而違約一方必須承擔悔約的後果。
有意見認為「這不符合當事人的意圖 」(Jolles, “Consequences of Multitier Arbitration Clauses”, 335), 但 須謹記法律上預設的爭議解決機制是法庭訴訟。作為法庭訴訟以外的例外情況,雙方當事人可以在同意的範圍內進行仲裁。然而,若出於任何原因仲裁不能在雙方最初設定的範圍內進行,無可避免地雙方須按照法律的施行回到法庭訴訟,而在此方面雙方的意圖是不相干。
正確的方法
仲裁是經當事人同意的爭議解決程序。仲裁協議可反映當事人同意進行仲裁。我等恭敬的陳詞認為,決定一項挑戰是否涉及仲裁庭管轄權的正確方法為考慮 (a) 該挑戰是否攻擊構成仲裁庭管轄權基礎的仲裁協議,以及 (b) (除了受挑戰的申索外)是否存在其他仲裁庭可以作出裁決的申索。
應用這個方法,C v D 案中的挑戰顯然涉及仲裁庭的管轄權:該挑戰攻擊仲裁協議,因為仲裁協議中的仲裁前要求據稱未獲遵守;除了那些受到質疑的申索之外,並無其他仲裁庭可作裁決的申索。
總結
鑒於仲裁作為一個受歡迎的爭議解決機制的重要性,而多重仲裁協議亦很普遍,無庸置疑,不遵守仲裁前要求的挑戰是否涉及仲裁庭的管轄權並須受到法庭審查是一個具有廣乏重要性的問題。C v D 案目前被上訴至香港終審法院。我等謹希望香港終審法院會為仲裁當事人就仲裁前要求的正確詮釋提供最終指引。
 香港中環雪厰街二號聖佐治大廈五樓503室
香港中環雪厰街二號聖佐治大廈五樓503室 +852 2868 0696
+852 2868 0696